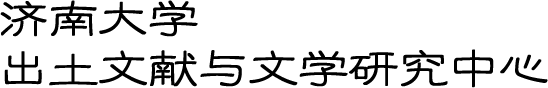《太一生水》宇宙生成论阐微
白奚
摘 要:本文讨论了《太一生水》中的重要概念“反辅”“相辅”“复相辅”的思想内涵与理论价值。“反辅”的观念强调在宇宙生成的早期过程中,被生成者反过来还要辅助生成者的生成活动,参与生成活动本身,从而使自己也成为一个主动的、不可或缺的生成者。“相辅”的双方“神明”“阴阳”“四时”“凔热”“湿燥”等没有主次之别,地位和作用是对等的。《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以“成岁”为终点,“岁”是五谷成熟的周期,同“水”有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太一”为什么要首先“生水”并“藏于水,行于时”。在《太一生水》中,农作物乃是万物的代表,“成岁”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待万物生成的,是以农为本的我国先民的哲学智慧,反映了先民对万物起源同水的关系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太一;反辅;相辅;复相辅;岁
作 者:白奚,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郭店战国楚墓佚籍《太一生水》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宇宙生成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凔热;凔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这是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完整、最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个宇宙生成论中,“太一”是起点,是天地间一切存在的终极根源。
从“太一生水”到“成岁而止”,首尾共九个“生”或“成”的环节。这九个环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太一生水”到“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再到“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这三个环节为第一个阶段,讲的是天地的生成;从“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到“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共六个环节为第二个阶段,讲的是万物的生成。这两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反辅”,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相辅”。“反辅”和“相辅”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含义和内容,需要认真加以辨析。
一 、“反辅”与天地的生成
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具有“初始”和“终极”两种最基本的意义。这两种意义在讨论宇宙生成论问题时是合一的,因为宇宙的开端即初始状态一定是具有终极性的,不可能在这个初始状态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初始的状态。换个角度来看,宇宙的开端即初始状态一定是某种终极性的存在,此即哲学上所谓本原,不可能在这个本原之上还有一个更加本原的本原。“太一”就是这个初始状态或本原,在宇宙的最初阶段,除了“太一”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太一”是一个绝对物,没有一个他物作为与它相对的存在,它是“无匹”的,而宇宙间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无匹的绝对物“生”出来的,这种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生”,在哲学上谓之“创生”或“化生”。关于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生”,庞朴先生有一个生动的解释,他说:“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生’,不是派生,而是化生。就是说,它不像母鸡生蛋、老狗下仔那样,生出一个独立于母体之外的什么第二代来;而是太一化形为水,绝对物化为相对,抽象固化为具象。”所谓绝对化为相对,在《太一生水》的文本语境中,是说绝对的、无匹的“太一”化生出相对的、有形的“水”;所谓抽象化为具象,是说形上的、不可感知的“太一”化生出形下的、可以感知的“水”。这一思路显然受到了老子哲学的深刻影响,受益于老子道论的思维成果。“太一生水”作为万物创生的第一步,相当于《老子》的“道生一”,由无形质的“道”下落到有形质的世界,没有这关键的第一步,万物的创生就永远没有可能。“太一生水”和“道生一”,虽然用词很不相同,但思路和方法明显是一致的,体现了道家学派在宇宙论上的理论传承和不断丰富、创新。
“太一”创生万物的第一步是“生水”,从生出“水”来开始创生万物的过程,是这篇珍贵佚籍最为独特的地方。“太一”生出“水”,是为了借助“水”来开始化生万物的复杂过程。为什么说“太一”必须借助于“水”才能创生万物呢?为什么“太一”不去像生出水来那样接着再亲自去“生”出别的东西?为什么“太一”生出“水”后不把继续创生万物的事情交给“水”来完成?我们可以借用上引庞朴先生的譬喻来解释这些问题。“太一”生出“水”,是“化形为水”,这标志着“太一”创生万物之第一步的完成,这个最关键的第一步是不可重复的,而不是像母鸡生蛋那样可以生了一个再生第二个、第三个。母鸡生第二个蛋是无需借助第一个蛋的,“太一”则不然,它生“水”是要借助于“水”,它必须借助于自己生出的“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生成活动。这也就是说,“水”被生出来后,还要帮助“太一”来完成下一个生成环节,或曰“太一”在后续的创生活动中还必须借助于自己所“化形”的“水”。这就是“水”对“太一”的“反辅”作用,离开水的“反辅”作用,“太一”创生万物的过程就无法继续下去。《太一生水》曰:“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太一”借助于“水”所生成的,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至关重要、至高无上的“天”。在这里,“水”是先于“天”出现的,在“天”出现之前,世界是一个“水”的世界。这在中国古代的所有宇宙生成论中是独一无二的,学界称之为“水生论”。
中国古代的思想是十分重视先后次序的,宇宙生成论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先出现的事物在地位上总是高于后出现的事物。在一般中国古人的思想里,“天”往往具有终极的、至高无上的意义,“天”不仅是亘古就存在的,而且世间的所有事物都被看成是存在于“天”之下,即所谓的“天下万物”。可是在《太一生水》中,“水”不仅先于“天”而存在,而且“天”的产生还必须依赖“水”的作用,这样一来,“水”的地位也就高于“天”了。这样的次序安排,真可谓惊天之论,对“天”的地位无疑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是《太一生水》这篇佚籍最具理论冲击力之处。这样的理论的出现,也表明彼时中国古代的思想界理性力量的高涨和传统“天命”观的衰落,这样重大的观念变化,道家哲学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反辅”是《太一生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是其特色理论。这一概念的关键,是强调在宇宙生成的早期阶段(生成天地的阶段),被生成者并不是被动的存在,不仅仅是被生成,而是反过来还要辅助生成者的生成活动,参与生成活动本身,从而使自己也成为一个主动的、不可或缺的生成者。这一理论是十分独特的,在《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中,“道”生出了“一”,但却没有“一”反过来辅助“道”的创生活动的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个直线式的、一路下降的过程。《周易•系辞上》中有另一个古老的宇宙生成理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是一个单程的、接力棒式的生成模式。《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是一、二、三……的单数系列,《易传》的则是一、二、四、八……的偶数系列,但是都没有“反辅”的思想。而《太一生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反辅”,则特别强调作为本始、本原的“太一”在后续的创生活动中还需要自己所生之物的辅助,离开了“水”的“反辅”作用,“天”将无以“成”,“太一”的创生活动将难以为继。这样的宇宙生成论比起《老子》和《易传》,显然更为丰富、复杂。
在“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之后,是“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在被生成了之后,还要反过来辅助“太一”来“成地”。“地”的生成离不开“天”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中,“天”和“地”都是同时出现的,故先秦时期的典籍中都是天地连称或并举。可是在《太一生水》中,却是先有“天”后有“地”,并且“天”还对“地”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一生水》的作者第一次思考了天地生成的先后次序这一前人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对后世的宇宙生成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淮南子•天文训》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天先成而地后定”,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太一生水》的出土,我们才得知这种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淮南子•天文训》还认为:“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之所以“天先成而地后定”,是由于重浊之气“凝滞”比较慢比较难的缘故,但是“地”的生成过程中并没有“天”的参与,“天”和“地”都是各自独立形成的,这同《太一生水》又是很不相同的。《太一生水》中还有这样的话:“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这种天在上地在下的观念符合中国古人对天地的空间关系的一般认识,但它又把“地”归为“土”而把“天”归为“气”,认为天和地是不同材料构成的。这种看法同上引《淮南子•天文训》把天和地的本质都归为“气”的观点不一样,但却同另一部先秦典籍《列子》的观点相同,《列子•天瑞》认为“天,积气也……地,积块耳”,“块”即土块,亦即“土”, 《列子》也是把“地”归为五行之“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太一生水》中,“地”的生成同“天”的生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并没有“水”的参与,而是后于“水”出现的“天”配合了“太一”,参与了“地”的生成。而“水”在“反辅太一是以成天”之后就不再直接参与后续的创生过程,可见在《太一生水》的理论体系中,“水”虽然很重要,但毕竟不具备“太一”那样的终极本原的地位。
值得重视的是,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中,“水”、“天”、“地”的依次出现都是由“太一”直接主导的,虽然有“水”和“天”的“反辅”作用,但“太一”对于天、地的生成始终是起的主要作用,所以《太一生水》才说“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这一思想很重要,是对老子留下的问题的一种解答。在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中,“道”生了“一”,然后由“一”去生“二”,再由“二”去生“三”,再由“三”去生“万物”,从“一”到“万物”的几个阶段,“道”似乎都处在隐身的状态,至少从字面上来看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老子的“道”在生了“一”之后就对后面的事情撒手不管了,我们宁愿相信“道”在创生万物的每一步骤中都在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但这一层意思乃是后人的理解,老子毕竟没有明白说出来。所以,“道”在万物创生的过程中是第一推动还是全程参与,这是老子遗留下来的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或许老子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太一生水》的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在他的文本里使用的不是“道”而是“太一”。“太一”生了“水”之后,是“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然后是“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成天”和“成地”的主导者都是“太一”。显然,“太一”并不只是第一推动者,而是全程参与并主导了天和地的生成。这样,《太一生水》的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老子留下的问题,虽然只涉及了天、地生成的阶段,但就其中的问题意识来看,无疑是对古代宇宙生成论的深化和推进。
二 、“相辅”“复相辅”与万物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中,天地的生成是重中之重,此前的一切都是在为天地生成做准备,天地生成之后,如《周易·系辞传下》所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万物在天地间的生成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天”和“地”生成了之后,接下来就进入了“太一”创生万物的第二个阶段。从“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开始,共有六个环节,其特点不再是“反辅”,而是“相辅”,即“天”和“地”、“神”和“明”、“阴”和“阳”等各个环节中对等双方的相互配合,实现下一个生成环节。这个阶段同第一个阶段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已不再有“太一”的直接作用,“太一”退居一旁,由自己的生成物“天”和“地”来“成神明”,然后“天”和“地”也退居一旁,由“神明”来“成阴阳”……,犹如接力棒的交接一般。
“相辅”和“反辅”有重要的区别,“反辅”的双方地位和作用是不均等的,有着主次之别,其中“太一”处于主导的地位,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水”和“天”都只起辅助的作用。“相辅”则不同,双方没有主次之别,地位和作用是相等的,“天”辅助“地”,“地”也辅助“天”,靠着双方的互相配合来实现“成神明”。“天地”之后的“神明”、“阴阳”、“四时”、“凔热”、“湿燥”都是这样。“神明”在这里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或复合名词,而是由“神”和“明”组成的并立的、可以相互作用的双方,“神”和“明”也要“复相辅”,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来“成阴阳”。因而“成神明”并不是成“神明”,而是成了“神”和“明”。接下来的几个环节“成阴阳”、“成四时”、“成凔热”、“成湿燥”、“成岁”也都是这样的。 “神”和“明”、“阴”和“阳”等双方的“复相辅”,就实现了从“天地”到“成岁”的一系列生成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从“天地”到“成岁”的六个相继的生成环节,其各个并立的双方的“相辅”作用中,都有一个“复”字,如“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等等。“复”在这里的作用和意义,学者们似乎大都没有注意到,极少有人做出解释。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这个字,如法国学者贺碧来指出:“我认为‘相辅’前‘复’字有‘更’的意义。” 笔者认为,尽管“复”可以释为“更”,其义与“又”同,但问题是这里的“复”如果释为“更”,其词性就是个语助词,起的只是加强语气的作用,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用于解释《太一生水》的“复相辅”似乎不合适。因而,这里的“复”字不宜作虚词解,应该有实质性的意义,即“往复”的意思,其义与《玉篇•彳部》所说的“復,返復也”和《易•复》的“反复其道”相同。《太一生水》的“复相辅”之“复”,即应释为“往复”、“反复”,指“天”和“地”、“神”和“明”、“阴”和“阳”等并立双方之“相辅”作用的重复进行。若此,则意味着这种“相辅”而生成他物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持续、重复方能实现。这也显现了“相辅”和“反辅”的一个重要不同,“反辅”这种作用和反作用似乎不需要重复进行即可完成生成的过程。为什么“反辅”和“相辅”之间存在着如此不同之处呢?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太一”生成万物的前后两个阶段中,前一个阶段是在“太一”的主导下进行的,后一个阶段则没有“太一”的直接参与。这样的安排用意何在呢?笔者以为,这可能是为了突出“太一”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终极原因的本原性作用,因为“太一”同“反辅”它的“水”和“天”地位不同,只能是“水”和“天”来辅助“太一”,而“太一”则不能反过来以平等的身份来辅助“水”和“天”。
三、 岁、成岁与水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解释万物的终极来源,多是从某个终极性的起点为始,而以万物的生成为终,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而《太一生水》却是“成岁而止”,没有讲到万物,这是不是话还没有说完呢?当然不是。中国古代的“岁”字有多种意义,其一是星名,即“岁星”或“太岁”;其二指时间意义上的年或年龄;其三指年成,如“国人望君,如望岁焉”(《左传》哀公十六年),“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管子·小问》)“成岁而止”的“岁”字在这里主要是用的第三种意义,除了表示时间的周期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示农业生产的有收成。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然界季节变化的一个周期下来,农业生产一定会有收成,这是人们赖以生存之本。这个意义上的“岁”,与“年”字的初始意义是一致的。“年”字古文作“秊”,象形兼会意,是由上面一个“禾”字和下面一个“千”字构成,此“千”字即是人身体的象形之简写形式。古人称禾谷一熟为“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收获时节,身负收割的禾谷,即是“年”,意为有收成。因而正常的年成亦称“岁熟”或“岁丰”,不正常的年成称为“岁凶”。而对于人类来说,作为“岁熟”的标志物的五谷,是万物中同人类的生存最为密切相关者,“岁”作为万物的代表乃是情理之中。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序列里,虽然没有提到万物,而是从“太一”到“成岁”,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事实上已经涵盖了万物,因为“成岁”的周期性持续,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重要的条件。在“成岁”的同时,所有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也都完成了它们生命的一个周期或阶段。因而,既已“成岁”,其他万物的“成”也就义在其中了。
事实上,《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在其他地方也提到了“万物”,其描述“太一”的运行时说:“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这里的“万物母”、“万物经”仍是在追问万物之所由来的问题,“太一”就是万物的终极来源。这里的“周而或始”、“一缺一盈”,似乎表明《太一生水》在这里不但是在追问万物的终极来源,还在表达宇宙万物运动的周期性及其表现形式,思考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存在的普遍规律。而“太一”的“周而或始”、“一缺一盈”,则可以看成是对“成岁而止”的继续思考,万物在“成岁”之后,还要在“太一”的主导和驱动下进行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周期性运动。这样看来,《太一生水》涉及的问题就不止于宇宙万物的生成,而且还包括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及其运动规律。事实上,在古代先哲们的思想世界里,宇宙万物的生成同其存在的状态和运动规律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需要一并思考并回答,只不过在回答的次序上有先有后而已。
细读《太一生水》关于万物生成的次序和各个环节的表述,会发现其中几个重要的环节都同“水”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以五谷的成熟为代表的万物的生成即“成岁”,都是离不开“水”的。继“四时”之后出现的“凔热”和“湿燥”两个环节都同“水”的存在密切相关,不经过与“水”密切相关的这两个阶段,“岁”就不会“成”。“湿”和“燥”指空气和物体中所含水分之有无与多寡,这里不必多说。“凔”的本义是“寒”,这个寒不是泛指的、只关涉温度的寒,而是专指水之寒或与水有关的寒,意为湿冷、湿寒, “凔”与“热”互为对文,表示与“水”密切相关的气温变化。农业生产经验表明,在一年四季中,只有经过了湿度和温度的节律性的变化,农作物才能生长以至成熟。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太一生水》安排“凔热”和“湿燥”作为万物创生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在为“成岁”准备条件。
对“凔热”和“湿燥”这两个环节的考察,还可以引发一些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推论。“凔热”和“湿燥”同“水”的密切相关性,使我们明白了“太一”为什么要首先“生水”。“水”在反辅“太一”生成“天地”后,并不是把生成万物的接力棒交给了“天地”便完全与己无关了,而是在后续的各个环节中都隐而不彰地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作为其最终结果“成岁”的载体的五谷,其生长和成熟也都离不开“水”。而“水”的这一系列作用,其背后还有更高的、决定性的存在“太一”,“太一”生了“水”,再借助“水”而生成万物,并主导着万物周期性的运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要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了。《太一生水》的宇宙万物生成论,从其起始点,到各个中间环节,再到最终结果,都贯穿了“水”的重要作用,所以人们才把这种宇宙生成模式归结为“水生论”。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凔热”和“湿燥”乃是 “四时”之节律变化的具体表现,“四时”变化的动力乃是“阴阳”之消息赢缩,“阴阳”的消长又是被“神明”所决定的,“神明”又是“天地”所生,综观这些环节可见,“天地”间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其最终结果就落实在“成岁”上,都是在为“成岁”准备条件。由此我们似可得到这样的看法:《太一生水》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思考万物生成的,它反映了以农为本的我国先民的哲学智慧。
水对于万物的重要性不仅在经验的层面最早被人们所重视,也引发了人们对万物起源同水的关系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各大区域都普遍存在。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就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思想,认为万物皆由水生成而又复归于水。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的这一思想的成因进行了解释,黑格尔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他说:“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个推测:泰利士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的养料都是湿润的,而温度本身也由这种(湿润的)东西生成,生物皆藉湿润以维持其生存。但是为一切事物所从出的那种东西,就是一切事物的原则。因为这个缘故,同时也因为一切种子都具有湿润的本性,而水又是一切湿润物的本源,所以他得出了这种思想。” 古希腊哲学家注意到了“生物”“种子”同水的密切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同《太一生水》的“成岁”联系起来思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从生物的生长来思考万物的起源的,都是把生物、农作物视为万物的代表。不同的是,在泰勒斯那里,水是万物的始基,水本身就是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而在《太一生水》那里,水对于“成岁”固然十分重要,但还只是具体的存在物,在水之上还有水之所从出的、终极性的存在“太一”。两相比较,《太一生水》的哲学抽象程度显然要高于泰勒斯一个层次。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